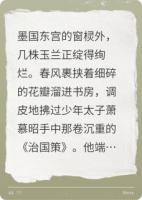电话被挂断后,我在原地站了很久。
直到中介小伙轻声提醒:
“阿姨,您的合同……”
我这才回过神,把那份卖房合同折好,收进用了十几年的旧布包里。
包里东西很少:身份证,病历本,还有一张塑封的老照片。
照片上,七八岁的张丽扎着羊角辫,一手牵着我,一手牵着她爸,在公园的樱花树下笑弯了眼。
那是她爸还在世时,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合影。
后来,她爸在工地出事,人没了。
赔偿款拿到手那天,我抱着刚上初中的张丽哭了一夜。
那笔钱,我一分没动,全存在一张存折里,封面写上“丽丽上学用”。
从此我白天在纺织厂挡车,三班倒,机器轰鸣震得耳朵快聋了。
晚上回家接缝纫零活,一件衣服五分钱,我做到半夜,手指被针扎得满是窟窿。
张丽争气,考上了省城的好大学。
学费住宿费,我一笔笔从那个存折里取。
送她上去省城的火车时,我把最后两千块钱塞进她书包夹层。
“丽丽,在学校别省,妈有钱。”
她抱着我哭了:
“妈,等我毕业赚钱,一定让你过好日子。”
我相信了。
后来她结婚,生孩子,打电话来说:
“妈,我一个人带不过来,你来帮帮我吧。”
我就来了。
这一帮,就是十三年。
刚到女儿家那年,外孙浩浩才满月。
张丽说:“妈,您有经验,孩子您多费心。”
于是那些年,我夜里从来没睡过整觉。
孩子一哼唧我就醒,喂奶、换尿布、抱着哄。
白天他们上班,我独自带孩子,洗衣做饭打扫,一刻不停。
可我没怨言。
我想着,女儿女婿上班辛苦,我能帮就帮。
直到浩浩三岁那年冬天,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,浑身疼得下不了床。
张丽早上出门前,看见我躺在床上,皱了皱眉:
“妈,您今天能送浩浩去幼儿园吗?我们早上有个重要会议。”
我有气无力地说:“丽丽,妈实在起不来……”
最后是李俊杰匆匆把孩子送走的。
出门前,张丽给我倒了杯水放在床头,说了句:“妈,您多喝水,发发汗就好了。”
门关上了。
我躺在房间里,第一次觉得,这个我付出了三年的家,好像并不需要。
而当天晚上,张丽下班回来,第一句话是:
“妈,浩浩的晚饭……”
我说我还难受。
她“哦”了一声,转身去厨房下了点面条。
给我端了一碗清汤挂面,上面飘着两片菜叶子。
“生病吃清淡点好。”
她自己和女婿,点了外卖,红烧排骨,油焖大虾,香味飘得满屋都是。
回忆戛然而止,去医院的公交车如期到来。
我麻木地上车,投币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,是王彩凤的朋友圈,这次是段小视频。
视频里,张丽正在给婆婆试戴另一条翡翠手镯,灯光下那抹绿莹莹得晃眼。
婆婆笑得合不拢嘴,张丽则对着镜头说:
“妈,这个更衬您肤色!买了!”
背景音里,销售员殷勤的声音传来:
“小姐真有眼光,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,二十八万八……”
视频到这里结束,车子在医院站停下。
我慢慢下车,脚步虚浮地走向门诊大楼。
我挂了个急诊号,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等待。
候诊区的电视正放着本地新闻。
我低着头,盯着自己磨破的鞋尖发呆。
一个熟悉的声音如冰锥,狠狠扎进我伤痕累累的心脏。
我猛地抬头,看见了张丽的采访视频:
“拆迁款拿到的第一时间,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父母。”